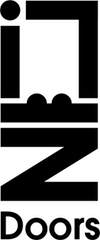拉菲姆·查达德出生于杰尔巴岛,是哈拉·斯吉拉(“小犹太区”)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从两岁起在耶路撒冷长大。2004年,他第一次回到突尼斯,并于2014年定居于此。在那里,他创作了一部关于记忆的艺术作品,讲述了该国犹太历史(世界上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几乎看不见的存在,他努力通过公共空间中的干预来重现这些痕迹,这些干预灵感来自人们、仪式、物品和材料,灵感来自消失的突尼斯犹太世界。
1940年代,北非国家的犹太人口超过50万,如今已减少到不足5000人。然而,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社区留下的痕迹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该国的音乐、美食和文化中,但都是无形的。据估计,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有超过10万突尼斯犹太人移民到法国和以色列。许多散居国外的犹太人再也没有回到突尼斯,但他们仍然对失去的家园充满怀念之情——这种怀念之情对于那些流亡在外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在这种背景下,拉夫拉姆的轨迹是颠覆性的、倒退的,甚至是越界的(上一代声称背弃了突尼斯的过去,在法国或以色列等地重建自己,但往往困难重重)。
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学者伊加尔·沙洛姆·尼兹里(Yigal Shalom Nizri)谈到从“超越时空限制的元空间”到现实空间中的日常生活。这与“像在突尼斯一样”这一活动标题遥相呼应,突尼斯犹太移民的子孙们往往在祖父母公寓中重现的小突尼斯或巴黎蒙马特郊区、贝尔维尔和萨尔塞勒等街区生活,通过美食、物品、仪式、信仰和所有流亡文化符号来延续他们的文化。与此同时,拉夫拉姆的举动以某种方式解冻了流亡时冻结的时间。他的做法绝非怀旧:这不是再现过去的问题,而是以一种鲜活、当下方式重新激活地方、物品和仪式。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谈到了拉夫拉姆的艺术是如何处理突尼斯犹太人消失的问题——以及中东地区当前事件对他的突尼斯实践的影响——但更广泛地讨论了这种艺术作品如何唤起普遍问题,如流亡、移民、边界的脆弱性和身份的可变性。